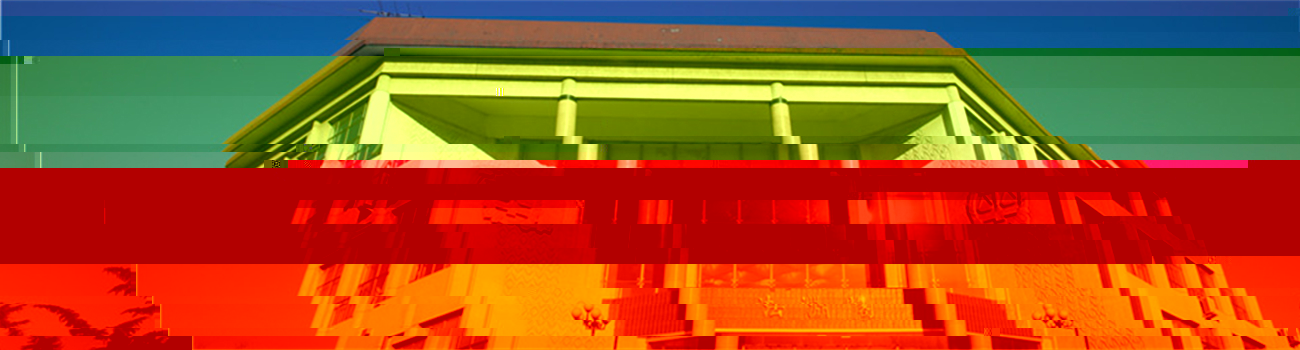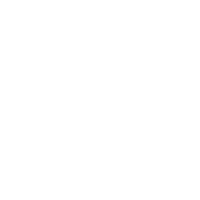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實施綱要研究,[1]既涉及到對中國法治建設形勢的判斷與戰略布局,也是對法學界理論智慧的一種考驗。如何使依法治國規劃課題研究與國家現階段改革發展的總體戰略思路相一緻?如何确定依法治國的階段性目标與長遠目标?如何制定可操作的實踐行動方案?這些問題都遠遠超出了法學書本知識的解答範圍,而與中國經濟政治社會協調發展和作為政治文明大國崛起的世紀性宏偉目标相關聯。因此,需要從國家發展的總體戰略來考慮。
一、依法治國總體規劃問題“規劃多少年”合适
(一)2020年是現階段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目标時間點。中央已經明确提出到2020年實現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标,并推出和即将繼續推出一系列改革發展的相關規劃部署。這是一個非常确定的、而且除非有重大時局變化、不會輕易發生改變的信息。目前距2020年還剩下将近十年時間。依法治國規劃課題理應對本世紀前20年戰略機遇期後一個十年的依法治國問題做具體規劃研究,圍繞構建和諧社會的階段性總體目标要求對法治建設相關問題做出積極回應和具體落實。這是法治建設與國家改革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總體進程協調一緻的具體表現,是一種比較理想的時間範圍。
(二)如果課題研究涉及的時間目标跨越2020年或不到2020年,都會出現政策依據不足、相關信息不足和目标設定困難的問題。把課題研究的規劃時間設定在2020年以後,則超越了現階段國家總體戰略目标的時間範圍,既在政治上缺乏必要依據,又存在設定一個什麼樣的目标的問題。如果規劃研究的時間目标不足2020年(即搞出一個依法治國5年規劃的研究課題),則又會漏掉一些目前已在國家部署之列的重要法治建設内容或是具有重要法治意義的改革措施,如2014年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及後續措施,2017年香港實現立法委員和行政長官“雙普選”,[2]以及更為重要的實現構建和諧社會的既定目标,等等。所以,隻要不與2020年實現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标時間相一緻,無論規劃課題的時間是跨越2020年還是在2020年之前,都存在一個究竟要确立一個什麼樣的具體時間點和設定什麼樣的目标的具體困難。這并不是說,法學界無法從法律改革的自身角度提出一些具體性的目标,同時也不妨礙法學界提出具體的法治改革目标時間表,而是說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這樣一種帶有總體性的宏觀目标受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總體目标的制約影響更大,更應該與國家的經濟社會環境目标協調一緻。因此,還是與國家改革發展的階段性總體目标相一緻為宜
(三)把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規劃研究的目标時間确定為2020年,不意味着對2020年之後的依法治國問題及基本走向不做前瞻性判斷(當然更不意味着所有法律改革事項都要規劃到2020年時完成)。實際上,隻有對本世紀中葉中國達到中等發展國家程度時的依法治國的可能狀态和實現水平做出前瞻性判斷,此前的階段性規劃研究才有明确的方向。但是,此種前瞻性判斷與階段性的法治規劃研究應該還是有區别的。
二、未來十年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基本目标是什麼
筆者認為,未來十年中國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主要目标或基本目标,應該是加強國家的法治能力建設。其基本依據是:
(一)中國仍然處于社會轉型中的矛盾上升周期,但國家法律治理能力的提升仍然不能适應客觀需要。2005年,筆者在《邁向和諧社會的秩序路線圖》一文中曾經提出:“中國社會仍處于矛盾的上升周期,尚未看到秩序出現良性拐點的迹象。”[3]5年來的形勢發展基本證實了這一點。在社會矛盾上升的同時,國家的法律治理能力下降、法律治理成本急劇攀升,應該是一個基本的事實。其中最突出的表現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員侵犯社會團體和公民利益的不合理規則措施時有出台,官員違法事件屢屢出現,“維穩”成本居高不下,依法“維穩”道路艱難。這是法律治理能力下降的突出表現。
關于國家能力不足問題,在九十年代,王紹光、胡安綱兩位學者曾經做了大量深入研究。筆者認為,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先後出現過兩種意義上的國家能力不足問題。一種情況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出現的國家财政能力不足問題。另一種情況是,自新千年以來,中國在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大幅提高的同時,卻又出現了社會治理成本(包括法律治理成本)大幅攀升、社會治理效果明顯下降和地方政府與官員違法追究愈來愈難的情況。
(二)社會矛盾上升、法律治理能力不足,這樣一種“問題”與“能力”之間的背離趨勢,很容易導緻社會矛盾向社會危機演變,最終危及政權的合法性。特别是,在過去十多年中,經濟增長的績效一度掩蓋了衆多社會矛盾,客觀上扮演着社會穩定器的作用。現在,貧富分化問題、經濟對外依存度過高、内需不旺等經濟結構的内在缺陷和金融領域的風險因素,已經使經濟增長從社會的穩定器變成了社會不穩定的又一個重要根源,經濟因素反而容易成為引發社會矛盾的導火索。這雖然沒有改變中國社會繼續呈現總體向好的趨勢,但問題治理已經不容再拖。
(三)從法治建設自身看,随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無法可依”問題逐步解決,法治發展在當前和今後面臨的突出問題,是“快速建立”的法律制度與法律秩序“緩慢生長”之間的矛盾,或者說,是要突出解決法治秩序的生長問題。[4]法治秩序的生長問題,也對加強法治能力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這預示着中國正在從以解決“無法可依”問題為中心的法治建設階段邁入以提升法治能力為中心的法治建設新階段。
綜上所述,未來十年中國的法治建設應該加強法治能力建設,并通過法治能力建設,推動中國社會順利跨越轉型風險期。
三、加強國家法治能力建設的主戰場在哪裡
國家法治能力,是現代國家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現代國家能力區别于傳統國家能力的重要标志。也許有人會說,加強國家法治能力建設,應該是全面地和全方位地推進法治建設和法律改革,不存在什麼主要領域或突破口的問題。從理論上說,依法執政、司法改革、法治政府建設、基層民主建設和樹立法律信仰等等,都是中國法治建設的重要内容,都應該全面推進,不應該有所偏廢。可以把上述改革思路稱之為“全面改革的思路”。退一步說,如果一定要區别出法治建設的主戰場,就應該以解決最具根本性的問題為主戰場和突破口。比如,從政治上說,加強中國共産黨依法執政是最具根本性和關鍵性的問題,應該以此為突破口。可以把上述改革思路稱之為“以中國共産黨依法執政為突破口的思路”。再比如,從法律上說,實現司法改革是法治的核心特征,應該以司法改革為突破口。可以把上述改革思路稱之為“以司法改革為突破口的思路”。
從理論上說,上述幾種觀點看似有理,但從實踐角度看,這些觀點至少均存在實踐的可行性和操作性的問題,有些問題在理論上也是有争議的。理由分别如下:
(一)未來十年時間相對有限,全面解決中國法治建設問題有時間上不可能。按中國現有的漸進改革模式的推進情況看,全面解決中國法治發展面臨的問題,真正實現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至少還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溫家寶總理在2010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的講話看中說,中國真正實現現代化還需要100年。[5]以此類推,中國的法治建設可能同樣需要上百年時間。至少,未來十年時間遠遠解決不了法治建設的所有問題,而隻能解決部分問題,或是在部分程度上解決問題。試圖把所有問題一齊列入議事日程,以一攬子改革方案解決所有問題,隻會使單位時間内的改革壓力過大,改革任務過重。這實際上改變了中國過去三十年改革的基本經驗做法,改變了漸進改革所遵循的“有所有為、有所不為”的做法。應該說,除非中國出現重大而緊迫性的危機,除非現有漸進改革模式的無法延續,否則,是沒有必要改變現有改革模式的。這是“全面改革的思路”不具有可行性的理由之一。
(二)在法學界可能提出的“全面改革的思路”中,有些改革項目的決策成本過高,一時很難形成成熟的決策,尚需在今後的實踐中不斷摸索嘗試。如鄧小平1986年9月3日在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人義勝時說:“政治體制改革的内容現在還在讨論。這個問題太困難,每項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廣泛,很深刻,觸及許多人的利益,會遇到很多的障礙,需要審慎從事。我們首先要确定政治體制改革的範圍,弄清從哪裡着手。要先從一兩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幹,那樣就亂了。國家這麼大,情況太複雜,改革不容易,因此決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較大以後再下決心。”依照鄧小平上述講話精神,與政治體制改革相關的許多法治建設内容,也同樣存在一個改革決策方案不成熟、決策成本過高的問題,需要在不斷的改革探索中逐步解決。這也是“以中國共産黨依法執政為突破口”的改革思路和“以司法改革為突破口”的改革思路目前仍不具有可行性的一個理由。即使從法學界的知識儲備和理論準備看,目前也仍不具備提出法治全方位改革方案的能力和條件。此種情況決定了未來十年法治建設同樣隻能選擇決策成本低的領域為主要着力點和突破口,或者說,以目前人們看得清楚的目标為突破口。
(三)改革資源的有限性和國内外環境的相對嚴峻性也決定了未來十年法治建設隻能有所為、有所不為。法治建設與其它領域的改革建設一樣,既需要各種支持性資源,也需要良好的外部環境條件。中國能夠用于法治建設的資源是有限的,包括政治資源、經濟資源、知識儲備,等等。其中特别是時間資源的因素。法治建設需要時間,法治秩序的生長需要一個自然的發展過程,包括法律規則的完善、法治政府的制度安排、官員和公民法律素質的提高、法律改革知識的儲備等。另一方面,中國的法律改革并不單純是一個國内問題,而往往與複雜的國際政治因素緊密交織,如何處理好法律改革和政治穩定與外部安全的複雜問題,處理好法律改革與國内、國際兩個層面相互交織的複雜因素的矛盾關系,同樣是一種艱巨的考驗。特别是近年來,随着中國經濟崛起的步伐明顯加快,各式各樣的遏制中國及和平演變中國的勢力也在加緊努力。改革資源的有限性與外部環境制約因素都使得中國法律改革,特别是法治“核心部分”的改革成為一盤交織中外複雜因素的大盤,沒有勝算的把握是不宜輕舉妄動的。
(四)遵循法治建設各方面之間複雜的生長時序關系與空間上的相互制約關系,要求人們要依循法治建設的内在規律行事。法治建設各個方面内容在客觀上不存在一個時間上“同步關系”和空間上的“并進關系”,而是呈現出一種更為複雜的生長時序與空間上的相互制約。比如,法律制度建設多具有快變量的性質,而制度績效和相對的法治秩序生長則具有慢變量的性質。過快的制度變革,如果不能迅速轉化為相對的法治秩序,不能産生立竿見影的效果,隻能讓社會公衆産生挫折感。同樣,自上而下的有序的民主化進程,應該以法治政府建設的成功為前提條件。否則,一個守法意識不強的政府反過來很容易成為民主選舉的“批評對象”,進而使政府喪失對民主化進程的領導資格。所以,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把握住法治建設的關鍵環節,把握好改革的次序與步驟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這些因素決定了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裡的中國法治建設,不僅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而且應該準确把握住制約整個法治化進程的關鍵性環節和前提性環節,集中力量争取突破性進展,進而為下一階段的法治建設打下良好的基礎。
以這樣的考慮看待法治建設的主戰場問題,本文的基本觀點是,法治政府建設(依法行政)是未來十年中國法治建設的主戰場。具體理由是:
1.把法治政府建設确定為法治建設的主戰場,與國家的既定決策高度契合,決策成本低。建設法治政府是我們黨和國家的一項既定決策,本身不存在決策成本問題。把法治政府建設“提升”為未來十年法治建設的主戰場,應該不存在重大決策困難。相反,如果把法治建設的其它方面作為法治建設的主戰場,即使從決策本身看,也需要一個複雜的決策過程和較高的決策成本。如把司法改革作為法治的主戰場,司法改革本身就存在較多的政治性争議,
如司法體制問題、司法“地方化”的問題等,都不是短時間内能夠迅速解決的。同時,雖然司法改革問題也是列人國家改革議事日程的事,但與法學理論上的期待相比,從已經提出的司法改革目标看,目前的司法改革仍然是一種有限度的穩妥改革。全面徹底的司法改革,應該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而後者的全面啟動,尚未全面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另一方面,司法機關在中國經濟社會生活中隻是起到一種局部性的作用,缺乏全方位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份量,所以,以司法改革為突破口提升法治能力建設,會有一定作用,但是作用有限。
2.加強法治政府建設對于提升國家法治能力、應對可能出現的社會危機具有直接的和全方位的重大意義。如果說黨的領導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領導力量,政府則是直接的實施者和推動者,也是應對各種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的直接負責機構。加強國家法治能力建設,提高應對各種可能出現的危機的能力,首先要加強法治政府建設,提升各級政府依法應對社會矛盾和問題的能力。
3.從制約當前中國法治化進程的全局性的主要矛盾看,法治政府建設滞後已經成為制約當前中國法治化進程的最主要制約因素。雖然國家已經明确提出不能因為追求GDP而犧牲環境與社會發展問題,但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内在财政沖動,仍然經常成為侵犯公民權利、破壞生态環境和犧牲社會發展的突出根源,政府行為違法和官員違法經常成為許多社會矛盾的引爆點。與此同時,法治政府建設的滞後也對法治建設的其它方面造成了多種負面影響。比如,地方政府違法和官員違法破壞了司法審判的大環境,政府違法成為地方各級司法在理論上應該面對但事實上又無力面對的難題。政府違法和官員違法也挫傷了二十餘年普法促成的公民的法律信仰,幾十年普法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法律信仰,往往被政府冗員的違法行為毀于一旦。所以,如果法治建設不能取得突出效果,把再多資源用于普法也是沒有意義的。
4.法治政府建設已經上路,應該也隻能繼續向前推進。2004年3月,國務院出台《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提出“經過十年左右堅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标”,具體包括七方面目标内容。[6]轉眼間,法治政府建設已走過6個年頭。從實施情況看,七個方面的具體目标距離實現尚存在差距,應該更加努力。即使能夠如期用十年時間(2004年-2014年)把相關制度建設的基礎性工作完成,由于制度建設與制度績效的顯現之間存在“時滞”現象,法治政府建設進入到“績效顯現期”估計也還至少需要再加上一個十年的努力。
四、把法治政府建設作為法治建設主戰場意味着什麼
(一)把法治政府建設作為未來十年法治建設的主戰場,意味着國家把法治政府建設視為下一階段具有全局性的戰略工作,需要以更大的決心、更強有力的措施和更多的資源用于加大落實《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
(二)把法治政府建設作為法治建設的主戰場,意味着其它領域的法治建設應該配合法治主戰場,以有限改革和有限措施促進和幫助主戰場目标的實現,既不拖後腿,也不過分超前。具體說,主要涉及如下幾方面的配套改革:一是繼續加強黨的依法執政建設。各級黨的組織、特别是地方黨組織,要規範地方黨委的決策,支持和配合地方政府依法行政,認真履行法定職能,承擔法律責任,同時支持地方人大對同級政府行使權力。二是繼續加強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進一步落實和加強地方人大對政府财政預算的決定權和監督權,切實行使好地方立法權,行使好對同級政府的工作監督權和人事任免權。三是繼續穩步穩妥地推進司法改革,通過行政訴訟來約束和規範政府的依法行政。四是繼續加強基層民主建設,以基層民主建設推動政府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設,加強社會對政府工作的監督。五是繼續有針對性地開展全民普法運動,把監督政府工作與保障公民權益的相關法律宣傳結合起來。
(三)把法治政府建設作為法治建設的主戰場,意味着要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特别是要改變各級地方政府單純追求GDP和法治建設為經濟發展“讓路”的不合理做法。意味着要讓各級地方政府切實承擔促進社會經濟全面發展和公共服務的職能,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意味着各級地方政府在處置公共事件和社會危機時要依法辦事,在法律權限内處理問題,增強處理和應對社會突發事件的法律能力。
(四)從長遠角度看,在初步實現“用十年時間建設法治政府” (2004年至2014年)目标的基礎上,再用5到10年時間繼續全力推進法治政府建設,使制度建設轉化為依法行政的良好治理秩序。其最終目标是在中國形成一個切實履行法律職責和嚴格守法的行政官員隊伍,将是中國法治漸進改革進程走向全面成功的關鍵性環節,也是下一階段中國政治民主化進程全面有序展開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