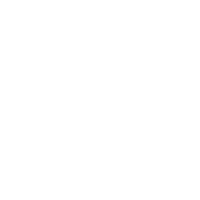踏進法學學府的那一刻起,我們開始不斷思索,法律人的使命應當落于何處?
我們在問:我們到底從何學起?該怎麼學?我們怎樣将學習、學生工作與生活真正平衡起來?我們怎樣邁向更遼闊、更廣袤的生命?
他們在答:我以自身生命觀照天地,願給你最真摯的分享;我以滿腔熱血投身學術,願述說求學以來用心貯藏的積澱;我以每一言、每一行為你舉起燭火,照亮彼此的一段旅程。
走進師者如蘭,于訪談與思索間,駕一葉扁舟,渡遠洋以遙望前途似錦,聞師道以辨明人生方向,共赴你我光輝未來。

1.您對法學的追尋之路是從法大開始的,您覺得您在法大讀書期間最大的收獲是什麼?
我覺得最大的收獲是能在一個比較好的氛圍中學習,并且在本科期間養成了比較好的學習習慣。當時有很多優秀的師兄師姐帶着學習,用自己的經驗指導我們,法學學習以一種類似同伴教育的方式進行。我現在也保持着向優秀的人學習的習慣。法大昌平校區雖然離市中心、離其他的一些學習資源、實體資源比較遠,但在這個校園内,通過類似這種同伴學習的機制,自己還是能有很多收獲的。
2.如今您仍在法大教書,您上行政法課的時候,看到台下的學生,有沒有覺得看到了曾經的自己?從學生到老師身份的轉變,帶給您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最大的感受是現在的學生比我們那時候優秀很多,比如像現在學生有很多模拟法庭活動,以前也有,但以前的模拟法庭基本都是表演式的,而現在對抗性更強、對專業知識能力的考驗更大。
學生的優秀在某種程度上也給我帶來很大的壓力。肯定有看到曾經的自己的感覺,但不是說看到曾經優秀的自己,而是看到自己當年學習的時候是什麼的狀态。對這種狀态最直觀的感受可能就是對于知識和更好的自我訓練的一種期待。
上課的時候其實不是向台下看,我常常覺得它是一種平視,在階梯教室就是仰視了。這種平視或仰視實際上是非常大的壓力,因為需要不斷地去考慮自己在講台上的正當性,怕站不住講台,講得不好被趕下來。
3.您和同學們是亦師亦友的關系,您會給自己老師的身份做一個什麼樣的定義?
我會和同學們共同讨論問題以及交流想法。我的期待是用一個朋友的身份和同學們相處,因為在知識和真理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甚至某種程度上現在的人和古代的人也是平等的。
在跟同學們的交流當中,我覺得對老師最基本的定義,就是和同學在求知方面平等的朋友關系。而且相當大的程度上,我也會從同學們身上學到很多的東西。比如我過去寫的一些文章,有的就來源于課堂上或課堂後同學們的提問。同學們會提出不同的意見,甚至是批評的意見,這些都是對于老師本身身份的一種定義。因為沒有學生就沒有老師,一個人不能孤零零的,不和其他人産生“法律關系”。老師的定義是由學生來定義的,反過來可能也是一樣,學生的定義也是由老師來定義的。學生和老師相互定義,誰都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
4.您現在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行政法,您當時為什麼選擇行政法這個研究方向?讓您堅定這個研究方向的契機是什麼呢?
最直接的一個原因是希望自己能在行政法的知識體系方面做點自己認為對的事情。
我讀本科的時候,行政法還不像現在體系相對完整。行政法的體系性相比于其他部門法要弱一些。在那個年少無知、年少輕狂的時候,覺得比如民法等部門法自己已經學得很好了,因此想挑戰一下,那就學行政法吧。特别是當時作為一個本科生,拿完江獎以後自信滿滿,于是就選了行政法,覺得能在行政法的知識體系方面做點自己認為對的事情。
另外一個原因是,當時的法治政府和行政法治的實踐狀況還不是很理想,大量的行政權力并沒有被關到制度的籠子當中。當時自己作為一個本科生,覺得可以學以緻用,特别是寫論文的時候,總愛說制度構建,覺得自己能構建一些制度,所以就選了這個方向。
5.您怎麼看待行政法作為公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的作用?
行政法是一個底線性的部門法。因為所有的部門法都需要講求法律主治,那麼兜底的作用可能就意味着為别的部門法律施行提供基本保障。行政法是規制政府的,當所有的主體,不管是普通人、企業、還是政府機關要守法的時候,政府守法肯定是居于首位的,不然上行下效,普通的老百姓就更不會守法了。所以我覺得這就是行政法在部門法當中最獨特的地方,它是守住底線的一個部門法。
6.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的同學很多到在大三才學習行政法,但卻已經要确定研究方向,如果因來不及接觸行政法而沒有以此為研究方向,您覺得對于很多同學來說算是一種遺憾嗎?
我覺得談不上遺憾,所有的部門法都重要,而且從比較法來看、從世界各國現狀來看的話,選擇民商事領域的法學生是相對比較多的,甚至會占到絕大多數,這和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的活躍程度是相關的。
第二點,所有的部門法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相通的。選擇一個專業方向,并不等于以後隻學這個,其他的部門法和基本的知識内容也需要涉及。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通常來說合同或者一個物權的生成,都是在民法當中讨論的,但實際上絕大多數國家的物權登記制度,都需要依托國家來完成。還有婚姻,這好像是兩個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私法上的事情,但實際上也有大量的公法的影響。比如結婚證需要到行政機關領取,這其中就有跟行政法有關的制度。
7.您做學術研究時除了行政法之外,也有其他的學術方面的涉獵。您覺得其他學術方面的涉獵對行政法的研究有什麼樣的作用?
最基本的是能夠幫助一個人發現問題。這個問題可以以此類推,在研究民法,甚至研究非法學以外的社會學、政治學、管理學等學科時,學科的交叉是必要的。最直接的一點就是幫助發現問題,看到具體的問題到底在哪裡。
比如以婚姻制度為例,民法和其他部門法都有大量的制度設計,訴訟當中也是如此。在民事訴訟當中,法官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判準許離婚,在法條上的體現可能很簡單,即感情确已破裂。但如何确定感情确已破裂呢?通過社會學的實證分析,我們會發現感情确已破裂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在現實中,法官可能是通過雙方聯系他的次數來判斷感情是否破裂的。其他領域當中同樣也是如此。比如刑事領域中,我們如何去判斷人身危險性。很多制度跟人身危險性是相關的,尤其在自然犯罪中。單純從法條中,我們可能很難理解什麼是人身危險性。但如果各位真的到監獄接觸過實施過暴力犯罪的人,到他面前坐一下,都不需要老師在課堂上講,可能在那坐着的十秒鐘就能懂得什麼是人身危險性。
這些知識是來源于其他的學科的,可能是社會學、政治學,甚至可能是語言學等,但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是要從不同的學科中都發現自己研究的領域的問題。
8.您曾經說過“選擇不難,堅持才難”,您覺得您在行政法學術研究之路上遇到的困難是什麼?
我覺得困難可能主要分為兩個方面吧,一方面是基礎理論研究的共性問題,另一方面是法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個性問題。
一方面,基礎理論研究的問題是所有學術研究都會涉及到的問題,在法學研究當中主要表現為法理學以及哲學方面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當然是很重要的,但往往很難帶給你太大的成就感,因為你可能會陷入其中,找不到出路。盡管你知道這裡面有問題,對它也感興趣,但是長期隻有投入,沒有回報。我猜想可能在自然科學領域當中也是如此,我們隻看得到做出成果的人,但是背後一定還有大量人、時間、精力的投入。很多人甚至将一生都投入到自己認定的某個基礎理論研究的路徑當中,可能研究了數十年以後又發現自己當初選擇的思路是錯的,那麼他以前的很多投入可能就白費了。我覺得基礎理論研究的問題是學術研究之路上的困難之一。
另一方面,我覺得是法學研究必然要面臨的理論和實踐的一種差異。這種差異并不是說理論都是對的,實踐一定是有問題的或是錯的,但至少有相當的情況是如此。面對這種差異你可能會反過來對自己原先所堅持的方法或者理論産生質疑,以至于想要放棄,繼而改換思路。
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選擇不難,堅持才難”。畢竟要做選擇是很容易的,每天都可以有新的想法産生,進而選擇去實踐新的想法。但是如果要求每天都向着同一個選擇努力,這種看不見希望的堅持就很難了。
9.您剛剛前面提到了兩個困難,一個是基礎理論方面的,一個是理論和實踐的矛盾。那老師是怎麼克服這兩個困難并堅持下來,或者說怎樣和它們并存着堅持下來的?
因為我年齡不算太大,所以可能不太敢說我真的“堅持”下來了,就是堅持到了現在,可能最多也隻能是說懂得和困難共處。卷也好,或者說困難也好,某種程度上是會和一個人共處一輩子的。即便沒有這種類型,也可能有那種類型,當然我指的是在學術方面或者在研究方面啊,生活當中就見仁見智了,不同人有不同的生活态度,我覺得都很好。
但對于做學問或者說做學術,還是會有一個共通的标準。因為學術成果不可能像孫悟空那樣突然從石頭裡蹦出來,它一定是要有積累的。一旦被打斷或者被破壞,想要再接續上恐怕就非常難了,所以我不敢說我堅持下來了,隻能說正在努力共處。
之前有一個老師跟我提到過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一句話,大緻說法就是好的時候當然特别好,那不好的時候呢,就想想好的時候就可以了。我覺得可以以此類推,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們就想想美好的時候,畢竟過去總會有比較美好的時候。好的時候當然是很好的,不好的時候想想好的時候就能夠積極樂觀一些,從而幫助我們更好地堅持下來。
10.您在讀博的時候,曾有到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訪學的經曆,這樣一段國外訪學經曆給您的學術研究帶來了什麼收獲?
最直觀的感受就是開闊眼界,這意味着你能夠了解到一類相對成熟的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大概是什麼樣子。比如,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的學生是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或者觀念不太一樣但是同樣都非常優秀的人,他們的思想相互碰撞時産生的火花,讓我感受到相當多元的文化氛圍。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比較特殊,他們曾經有個院長的一個理念就是要用一群優秀的人組成一個優秀的學院,包括學生也包括老師。像同學們所熟悉的博登海默,職業生涯後期就是被這麼一個理念延攬過去的。這樣的理念是有其合理性的,因為有時候不需要有老師過多的規劃或安排,隻需要把優秀的人湊在一起,他們自然而然地就會産生出很多好的成果或好的想法,也就能夠去實現目标、創造成就。在許多有比較成熟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的國家,它們的圖書館是24小時開放的,不存在所謂的熄燈時間,當你刷卡進去的時候,燈就會亮起。你會看到在這樣一個地方,相當多的優秀的人聚集在一起,大家充滿對于求知的渴望。
第二個直觀的感受就是他們的教學方式和學習強度跟我們有很大不同。我們常說國内現在很“卷”,其實去了以後發現他們的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學生更卷。以憲法、财産法為例,他們一周同樣是3、4次課,每次課是45分鐘,但不像現在包括法大在内的很多院校一門課三小節一次性上完,他們會拆分成2、3次在一周内上完,每次課後面的閱讀量是不小的,大概是50~100頁的英文案例閱讀量,帶給我完全不一樣的感覺。以及他們課堂當中的訓練方式也是一種高強度的、拷問式的學習體驗,會有很多提問環節。我當時很感歎原來法學教育也可以是這個樣子的。
這是我對國外一些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比較直觀的感受和收獲。
11.那在您體驗了美國加州大學的學習方式後,他們的教學模式對您現在的教學方法有影響嗎?
影響我覺得主要有兩方面,更多是體現在教學理念上。
一方面我會希望能夠更多地聽到同學們的想法,也會鼓勵同學們相互之間讨論或者來和我讨論。但反過來講,不同的國家甚至不同的學校都有自己的特點,法大畢竟法學專業的學生比較多,課程安排會大課為主。在這種情況下,想要有更多的讨論就比較困難。因此我覺得也不要完全照搬,那樣反而會降低同學們的學習效率。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會充分相信同學們的學習能力,沒有必要手把手地教大家怎麼學。其實大學學習本身就是一個有組織的自主學習的過程,這種組織來源于老師,比如說布置相應的文獻閱讀,配套相應的案例分析。但我不會把所有的想說的話都說出來,我會留白,比如我隻講百分之七十,剩下的内容以提問形式呈現但不回答。在這種模式下,我相信,也能夠在近幾年教學過程中發現,大家自然而然地都會産生自己的思考。其中還有一部分同學會把其中的問題轉化出來。比如說有的同學受到問題啟發去寫一篇論文,去參加一些比賽投稿等等,做得也都很好,之後還會跟我反饋說這個問題是來源于當初課堂上某個沒有答案的提問。我認為這些現象都說明我的這種教學方式是可取的,我也從跟同學們的交流中收獲了很多。
12.經曆了這麼多年的學習生涯,從國内到國外,您為什麼最終會選擇回到法大?
很直接的一個原因,是我的指導老師張樹義老師,當時希望把我留在法大教書。我相對是比較随遇而安的,不會太執着于一些事情,但是碩士研究生包括博士研究生的指導老師,對于一個人的成長,尤其在20到30歲之間,影響還是很大的,所以我決定留在法大教書。
13.您可以分享一下張樹義老師在哪些方面對您産生了影響嗎?
最直接的一點是要認真教學,一定要站得住講台。我記得快要博士畢業的時候,我做過一次非正式的講課。講完以後自己很興奮開心,就跟樹義老師彙報了一下,說以後有機會的話,希望這個狀态能夠一直保持下去,當時很自信地認為自己對教學不會有一種疲憊感。然後樹義老師回了一個短信,他說他把講台視為是一個揮灑生命的地方。這句話對我影響很大,尤其在自己要從學生的身份轉向一個社會職業的身份的時候。
後來自己真正教書了,一開始有幾次差點遲到了,後來和樹義老師順口說了,被老師嚴厲批評了。他說給學生上課怎麼能遲到,提醒我授課一定要認真,一定要站得住講台,不然實際上是誤人子弟。
14.面對未來多元的職業規劃選擇,您覺得同學們應該懷着怎樣的信念去規劃自己的學業與未來呢?
法學專業的學生本身是一個共同體,共同體有個名稱叫法律人,所以從信念的角度來說,第一點是要時刻看到不公。不管做哪一個行業,律師、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立法工作者、企業的法務,再或者跟法律沒有直接的關系的職業,這一點都是必要的。法律本身就是公平正義的代名詞。對職業規劃的某種程度上來說,關注不公也是一種新鮮感,會讓自己在從事這個職業時更有成就感。
第二點在于要有更多的共情。作為法律人,要跟不同人打交道,意味着要時刻留意和提醒自己,要有一種代入感去了解别人的想法,然後再根據自己的職業特色去處理設計。
第三點是不要太執着。因為有時候太執着的話,難免會陷入一個怪圈。我跟我自己的研究生也是這麼說的,學習當然很重要,但是必然會面臨一個問題,我真學不下去怎麼辦?學習讓我不開心怎麼辦?我覺得不用太為難自己,最重要的還是要保持自己的平衡,不管是自己眼前要做的職業規劃中的事,還是自己的生活。有了這種平衡,在職業上可能才會做得更好。我個人的體會是要保持好自己的心态,平衡好工作和生活的關系。
15.我們在座的有些是大一的同學,剛剛進入到法大學習,您對他們在學習還有生活上會有什麼樣的建議呢?
我們都知道中學的時候計劃、安排相對比較簡單,因為目标比較單一,往往隻要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文化課學習上就好。但大學實際上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條賽道,如果你覺得專業課學習上的内卷讓自己感到過分焦慮,那你可以去試着做其他的事情,比如你可以參加辯論賽、體育活動、法律援助等等,甚至你可以就學好某一門外語,再或者是參加一些其他類型的校外活動。這些活動就是不同的賽道,它同樣可以讓你很優秀,從而緩解你的焦慮感,說白了就是你可以換一個賽道去卷,這可能就是大學和中學最大的不同點。但是這個不同點有個前提,那就是你要安排好自己的時間,并且做好未來發展的大緻規劃、明确一定時期内的目标。
過去常有同學會來問我,自己想做的事太多或者任務安排太緊,時間不夠用怎麼辦?我常常會反問的一句就是,你今天早上幾點起床?當你覺得時間不夠用的時候,你為什麼不早點起床呢?我知道現在很多同學都習慣早上八九點起床,選課排課表的時候也會盡量避開早八。但如果你六點起床呢,是不是一下就多了兩個小時出來做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早上6點起床,然後晚上不要睡得太晚。這一來是一個時間安排的問題,二來我想對于絕大多數同學來說也是一個良好的一個作息習慣。這是一種長期主義,也是做好未來一切規劃的起點。
其實做任何事情都是這樣,比如說足球運動員當中運動生涯比較長的C羅,還包括原來的籃球運動員科比,他們在職業生涯中都是相當自律的人。以此類推,我覺得在還不到20歲的這個時候,有一個好的自律習慣,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法律中常常會講主體客體,那我們就不妨把自己看作是主體,把自己的身體看作是客體,然後盡量把自己的客體的活動安排好。
在此基礎之上,我還想給大家的建議就是各類的書要多讀,不要僅限于法學這個學科或者教材這種類别。就跟前面的問題一樣,其他學科的知識對我們理解社會現象和法條是有幫助的。比如說如何理解結婚年齡,如何理解婚姻,是否需要離婚冷靜期,如何理解這個國家對于家庭的一種介入等等,廣泛的閱讀會給我們提供不一樣的視角和幫助。
再就是學好一門外語,這對于各位同學而言會有很大的幫助。因為全球化、國際化的趨勢可能會有波折,但是它不會中斷。在國内說到國家利益的時候,可能隻有比較字面上的理解。但是如果你有一個好的外語基礎,換一個環境生活學習的話,你自然而然就能理解國家利益的含義了。
再者就是練好一個體育項目,哪怕是跑步。我相信這個習慣也會給大家未來幾十年的生活帶來很多益處。尤其大學比中學多了很多時間和條件去練習、去嘗試。我上大學的時候就經常會踢足球,之後也會跟同一個社團的同學打乒乓球。運動帶給人的好處是多方面的,除了提高身體素質,它還能幫你合理釋放壓力,讓你有一個好的精神狀态去更好地投入學習和工作。
16.老師您剛才提到了幾次“卷”,那麼大一新生前剛從高中生活的“卷”的氛圍中跳出來進入了大學,剛才您也說在您求學的時候,法大就是一個比較“卷”的地方了,您怎麼樣看待這種現象呢,同時我們應該怎麼樣去調整自己呢?
全世界的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都很卷,這是我最直觀的感受。口頭上說法學教育是精英教育,但我覺得本質上不是。恰恰因為法學教育是一種職業教育,“卷”才是必要的,就好比學醫。什麼叫做職業教育呢?我覺得最直接的一點在于它的精神底色,那就是專業主義。如果這個專業你學不好,你以後要真正進入實踐的時候,你會猶豫甚至退縮。所以我覺得卷是來自于專業主義的訓練,而且是一種高強度的訓練。
各位現在理解的這個卷,我覺得更多是想要同時把很多件事情都做得相當好。部分同學想要兼顧各種活動、競賽,再加上學習,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覺得大可不必,因為隻要踩準你自己的專業屬性,而專業屬性的訓練未必是一定要通過某種競賽來去證明自己,你完全可以基于既有的經驗比如師兄師姐的分享,又比如老師的指導等等,找到一個範本去學習和訓練。所以要說卷的話,世界各國的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在這個意義上都是卷的,而且我覺得這種卷是有必要的,它是培養你日後的過硬職業素養的必經之路,是為了你在真正成為律師、法官等之後能夠堅定、自信地發聲。
那如何去平衡好學習和生活呢?我覺得學習歸學習、生活歸生活,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業餘愛好和自己調适的方式。有的同學覺得專業學得很費勁或者很枯燥的時候,去做做自己愛好的事情他就會很開心,比如我前面講到的運動。我覺得這就是一種平衡的方式。
當然也有一種情況就是确實不喜歡這個專業。我覺得首先要試着從中發現感興趣的點,如果确實沒辦法發現自己興趣的話,那做一點自己真正感興趣的事,這也是非常好的。我原來帶的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的學生當中,就有一位同學對法學就沒什麼興趣,他感興趣的是另外一個可以說跟法學不怎麼沾邊的領域,所以他從大一開始基本上就在那個領域當中投入很多精力也能獲得很多快樂,而且他畢業以後就從事這個行業,在這個行業中展現出了自己的才能,做得非常出色。這就像換了一個賽道跑步,關鍵點在于找到讓自己開心的、自己感興趣的領域,還要考慮畢業以後的規劃。也就是說,我們要認清法學對于專業素養的高要求,但同時也要清楚自己想要什麼、适合什麼,這樣各位同學即使面臨困難、面對内卷,也能夠比較從容鎮定地應對。
結語:張力老師的法學之路從法大啟程,十年求學路漫漫。他說,選擇不難,堅持才難,于是他選擇了留在法大,堅守三尺講台。他說,在知識和真理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他是老師也是朋友。他說,要看到不公,要學會共情,要保持好自己的平衡。法學研究的漫漫求索中,他如燭火引領前路、使人奮進;生命完滿的孜孜追求中,他如汪洋觀照天地、包容啟迪。